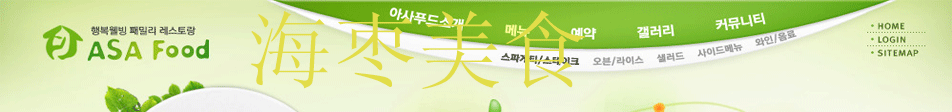|
编者按:不久前,数位中国诗人前往俄罗斯出席活动,展开交流。诗人韩博就此行写下长文《莫斯卡的狄奥尼索斯》,诗歌在一束光分四次连载,希望小伙伴们喜爱。 莫斯科的狄俄尼索斯(一) 普通的尺子与红色的楔子 我累了,今天不去酒吧。 好的。玛莎说。她站在我的身后,她的身后是一些急匆匆将饼干、香肠和啤酒塞进胡子拉碴的两道缝隙之间的艺术家。我坐在长条凳上,正心不在焉地聆听一首俄语的声音诗歌。约瑟夫·布罗茨基认为,俄语这种拥有无穷字尾变化的交流媒介,能够表达人类心灵最细微的差别,并且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伦理敏感度,因而具备成为文明载体的一切必要条件。可惜的是,我对于源于希腊字母的三十三个基里尔字母的变体的认知程度,不亚于苏美尔人留在黏土泥板上的楔形文字,更别提它们那些气象万千的排列组合——在这座丝毫也不顾及国际旅行者感受的欧亚帝都,就连地铁路线图中标注的站名都足以连缀而成巨大的谜团。我只背下来两个:“白俄罗斯站”,它邻近我落宿的酒店;“马雅可夫斯基站”,贯穿它的绿线通往红场,我喜欢那一堆彩色的葱头教堂,尤其是内部的壁画。壮阔如运河的街道上见不到什么英文字母,仿佛布罗茨基的童年记忆依然有效:他的小学教室中,“一张有两个半球的地图,只有一个半球是合法的”——资本主义世界使用的英语自然是非法的。既然如此,那么,我究竟在听什么?接二连三登场的俄国诗人并未致力于凭借俄语赞颂俄语,他们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一百零一年前瑞士苏黎世伏尔泰酒馆中的朗诵者,他们的声音反对意义,也就是说,那些声音似乎打算成为拆毁文明载体的一切必要条件。 玛莎又拍了拍我的肩膀:韩博先生,你确定不去酒吧? 是的,我确定。 好的。玛莎消失了。然而,过了一会儿,她的头又凑了过来:韩博先生,据我所知,杨小滨先生已经到达酒吧了,你真的不去吗? 还有谁在那边? 只有杨小滨先生。 我不去了。 好的。 可是,这一回,全名为丹多科娃·玛克萨拉·尤丽耶芙娜(DondokovaMaksaraYurievna),居住在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任教于其首府的乌兰乌德大学,以研究当代汉语诗歌为业的俄罗斯蒙古族女士根本就未曾离开半步,她再度催问,仿佛医生催问不肯直面病情且拒绝服药的患者:韩博先生,你真的确定不去酒吧? 好吧。你赢了。 患者站起身来,准备穿外套。 把左手套戴在右手上,如果有的话。 这是我来到莫斯科的第三个夜晚。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百卉凋敝,雪绒飘零。 说来也巧,此刻,恰恰是十月革命百年之后的第一个十一月底,刚刚登陆二零一七年的冬雪与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泞笼罩着这座城市。所谓太阳,一如开放于一八六四年的莫斯科动物园里的北极熊——它当然存在,但终日冬眠,毫不理睬跺着脚呵着气哆哆嗦嗦前来的观众们。我感觉自己已然身处一线幽深的洞穴之内,要么就是废弃的矿坑:上午九点,天未亮透,下午四时,夜又黑沉,二者之间,并无蓝天或晴朗那一类虚构之物,铅灰色的长空焊接着铅灰色的硬地,焊接着硬地之上档案一般的二十世纪筑物——无论是城市中心斯大林巴洛克风格的苏维埃哥特尖塔,还是郊区边缘失败包豪斯版本的三层红砖筒子楼——整个世界仿若一块生铁,人与自身、人与他者、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皆修建于此,径以盲人摸生铁的感受力为限,洞穴或矿坑之内的存在摩挲生铁的冰冷与粗糙,揣测生铁的重量及密度,知其不可知而格物致知,致知而致不可知之新的神秘。 我不禁翻检记忆:俄罗斯予我的想象,难道不正是如此?就像早期的基督教和佛教,皆可视为希腊化之产物,我自己的童年,未尝不算是一种苏联化的结果。我一度误将十月革命当作欧亚大陆北部帝国的历史开篇——那是在我开始攻读《水浒传》的年纪,据说那本书好就好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事实上,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就连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都搞不清楚,更别说通过课本发现二十世纪之前的俄国。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提及一条卡夫卡式的蓝色横纹,它位于“拉毛粉饰墙”的“与眼睛齐平处”,“两英寸宽”,从教室里出发,“准确无误地贯穿全国,如同一条无穷的公分母线:在大堂、医院、工厂、监狱、集体公寓的走廊”,“我没有遇见它的唯一地方,是农民的木屋”。在我的记忆中,那条横纹也刷进了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横纹统治的空间面貌与布罗茨基的描述大体相仿:一堵墙从地面开始“涂着老鼠灰或绿漆,而这道蓝纹就在它上面,蓝纹之上则是处女般纯洁的白灰泥”。布罗茨基说,一生中不知有多少次发觉自己机械地盯着它,“有时候把它当作海平线,有时候当作虚无本身的体现”,“它太抽象了,谈不上有任何意义”,“没有人问为什么它会在那里”,“也没有人能够回答”,“它只是在那里,一条边界线,灰与白、下与上之间的一道分隔线”,甚至“它们本身不是颜色,而是颜色的暗示”。的确,那条线的确太抽象了,乃至于当我长大成人之后,开始将它以及墙上的色块与至上主义者卡西米尔·塞文洛维奇·马列维奇的脑中之物联系在一起,他的画笔分泌出的单纯简约的几何罗列预示了从达达主义到极简主义的接踵而至。二十世纪欧亚大陆北部的室内空间属于达达或极简?有意思的是,原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列宁,可谓货真价实的达达主义邻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欧洲流亡艺术家们汇聚在苏黎世镜子胡同一号的伏尔泰酒馆,拒绝接受语言的符号能力,试图回归语言的基本单位之际,这位从事政治写作的流亡者,正租住在从酒馆门口扔块石头就能砸到的镜子胡同十四号,奋笔疾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用不了多久,他的画像就将挂遍失去锁链的无产阶级所缔造的那个横跨十一个时区的“新世界”,而在另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张可以清晰地映出鞑靼人的影子的俄国脸将闯入更多时区的室内空间。 “也许唯一能够扰乱”墙上颜色分界线的,“就只有一些替代性的棕色块:门”,“紧闭的,半掩的”,“透过那些半掩的门,你可以看见另一个房间,同样被分配了灰与白,中间一道蓝纹。再加上一幅列宁画像和一张世界地图”。布罗茨基将至上主义还原为现实主义。悬挂在我头脑中的画像,多于布罗茨基的世界,共有五幅,达达主义的邻居不过是其中的第三位。 两个小时之前,一辆内部座椅设置类似伦敦出租车(更接近厢式马车)的七人座“奔驰”,将我们运输至诺沃里亚赞斯卡亚街。下了车,穿过树木高拔的社区花园,来到一排马厩似的长条形平房面前,拉开遇见的第一道保暖门,里面却是一间酒吧。噢,它应该算是作为形而上学目的地的“兹韦列夫当代艺术中心”之侧翼——当然,也可以倒过来说,二者互为侧翼,因为“中心”的面积不过一间教室的大小。 几位俄国老艺术家正在酒吧的侧翼里忙碌着。确切地说:缓慢地忙碌着。依照“第十届国际莫斯科诗人双年展”官方节目单所列之时间表,还有十几分钟,一场名为“信息与符号”的“中俄视觉艺术诗歌晚会”即将开始,而布展尚未完成,至少三分之一墙壁还空着。不过,幸运的是,我发现自己带来的“柏林系列”——创作于五月至七月的纸本拼贴作品——已经上墙。那些脱胎于超市购物袋、杂志内页、街头海报和展览宣传卡片的植物纤维合成之物被小心翼翼地别上回形针,挂在高处的细铁钉上,一字排开,就像八十年代国营商店里的彩旗。它们的下方,是我的几幅小油画,同样一字排开,不是挂在墙上,而是斜倚在向室内凸出的墙腰处,仿佛几位慵懒地晒着太阳的闲人——当然,冬日莫斯科的真正阳光即灯光,冷光灯管。 前一天早上,我把装有作品的旅行箱交给工作人员,询问她们:需要帮忙布展吗?结果——自然没有回音。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展览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直到拉开形而上学目的地之门的那一刻。嗯,也不错,没有辜负斜坡上的镜子胡同。欧阳江河带来的书法作品也是如此展示,不是贴在砖墙上,就是摊在木桌上。他正大声宣布着价格:五万人民币一尺,不信可以去查拍卖纪录。我想,那些俄国艺术家如果听懂了汉语,或许会对这个数字目瞪口呆。其余的墙面上,除了从容带来的几幅纸上水墨小品(她要求从入口处更换到摆满食品的冷餐桌附近),就是本土艺术家的拼贴作品,介乎达达主义与构成主义之间,似乎更构成主义一些,仿佛亚历山大·罗德琴科就混在我们中间——作为构成主义的践行者,他经常挪用达达主义的照相拼贴技法,为弥赛亚式的共产主义制作宣传海报、杂志和书籍,他也是曾经的未来主义者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好基友,据说攻打冬宫的水兵便以后者的诗句“你吃吃凤梨,嚼嚼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为战歌,二人不时合作,一道替新政权擂鼓助威,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二五年发表了长诗《列宁》,但在一九三零年选择举枪自杀。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国家博物馆中,藏有罗德琴科针对诗人“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的名篇《关于这个:致她,也给我自己》创作的硬纸板上照片拼贴作品,共计十一幅,每幅皆配有诗句,比如“这一世纪屹立不动/一如往昔时代/不加鞭策/沉溺于居家琐碎的母马便不动”。诗篇和拼贴均指向马雅可夫斯基的情人,莉丽娅·布里克,一位有夫之妇,据说他们的私人关系径以政治信仰为春药。布里克也是罗德琴科的长期缪斯,她的美貌(当然,还有革命精神)使其不断出现在构成主义者迎合新政权需要而持续创作的适合大众传播的平面作品之中,成为苏维埃俄国艺术最值得回顾的经典形象之一。 罗德琴科好像就坐在前排的长条凳上。还魂的他,借由一位后生晚辈之口,对于“从镜子胡同一号扔块石头就能砸到十四号门前”的说法表示不满,至少也是认为不妥。我为什么如此口无遮拦?因为我走向话筒之前半个小时,中文名取作“玉立”的尤利娅·库兹涅佐娃(YuliaKuznetsova)非常紧张。我告诉这位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汉语语法教师:自己以为今晚只是一个展览,并不知道需要发言。她焦虑地说:这怎么办呢?你带了与视觉艺术有关系的诗歌吗,你也可以朗诵?没有。那可怎么办呢?她那张纯粹的俄罗斯脸(如果不考虑鞑靼人和蒙古人的基因悬念)都涨红了。我觉得有义务帮助这一位做事极其认真乃至于“轴”的诗歌节志愿者走出困境——对于汉语文学,我们毕竟拥有共同的偏好:她正在研究高行健的戏剧。于是,我耐心倾听了几首听不懂的声音诗歌,查看了几首看不懂的图像诗歌,于是,我明白了那些白头发的俄国人究竟在鼓捣什么玩意——去年冬春,瑞士达达主义百年大展期间,我遇到过许多类似的东西。于是,我决定聊一聊原教旨主义的达达与修正主义的达达。于是,我提到了那块并不存在的石头,比喻意义上的石头。我甚至开了一个玩笑:列宁的社会革命作品其实很达达,中国模仿俄国,作品拼贴得更达达。不过,也许列宁真的欣赏达达,时常出现在他的斗室五十米开外的那些流亡艺术家,也是真的厌恶资产阶级——至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此。埃尔·利西斯基创作于一九一九年的海报《用红色楔子击溃白色》,完全是一幅至上主义与达达主义的杂交品种,它传递的是“红军战胜白军”的官方政治信息。不过,列宁去世之后,这样的艺术手法就不再受待见了,“现实主义”——遭到狭隘理解的“现实主义”——取得了统治地位,二三流作家和艺术家凑成了官方审查力量的核心。赫晓鲁夫曾经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闭幕前夕召开的一个特别会议上,宣读了列宁谴责斯大林的政治遗嘱,在其附录中,列宁将斯大林称为“乡巴佬”——看来他说得没错,至少在文化层面——建议同志们找到一个“更为包容、更为忠诚,对党内同志也更有礼貌、更加关心”的人选来取代格鲁吉亚鞋匠儿子的党总书记职位。不过,自一九一七年起坚定地追随列宁的同志们,并未能实现苏维埃创建者的政治遗愿,因为他们之间的大多数,并未能熬过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早就遭了鞋匠二世的毒手。二战之前的十五年,被布罗茨基不乏审慎地称为“也许是俄罗斯整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句话出自《哀泣的缪斯》,一篇关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文章。而那位原名为安娜·戈连科,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女诗人,可谓领受了一份典型的斯大林时期的知识分子命运:第一任丈夫,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遭安全部队处死,儿子列夫·古米廖夫被送进劳改营,第三任丈夫,艺术史家尼古拉·普宁死于狱中。阿赫玛托娃的朋友们日子也不好过,包括诗人弗拉基米尔·纳尔布特和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在布罗茨基写给曼德尔施塔姆妻子的讣文中,开篇即提及:“……那个政权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制造作家的寡妇的效率如此之高,以至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她们的数目已够组织一个工会。”实际上,“最黑暗的时期”何止十五年,据伦敦大学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所著《俄罗斯史》记载,“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五三年,几乎每一个家庭——尤其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家庭——都至少有一个成员遭受了牢狱之灾,或是被流放到令人绝望的不毛之地”,亦即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曾经多次陪伴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访问莫斯科的米洛凡·吉拉斯如此写道:“斯大林知道自己是有史以来最残忍、最专横跋扈的领袖,但他一点都不为此感到担心,因为他坚信自己正履行历史赋予的使命。”“历史”是十九世纪以来的一项重新发明,摆弄它的“科学怪人”模仿基督教的末世论,将其改造为单向线性运动的发条机器,设定目的决定手段,任何手段,只要吻合目的,即为合法,由此抛弃了罗马法律传统的政治伦理,抛弃了“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人类生命是神圣的”之类个人主义腔调。布罗茨基借《逃离拜占庭》记下:斯大林在“大清洗”期间宣称“对我们来说,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人类生命在本质是不足挂齿。 今日莫斯科街头,我没有遇见一座斯大林雕像,无论大小,它们似乎已被拆除得一干二净,就像部落时代的血亲复仇那样。然而,列宁的形象还在,尽管不再是坦克之上登高一呼,仅仅默默旁观着商业街上的人流。历史正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俄罗斯的现代传统,那是彼得大帝以来的传统,窗口开向西方,而不仅仅是泛斯拉夫主义,更不是建立在“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基础之上的“世界和平”。 十八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化深受一种强烈的补偿心理驱动,究其历史根源,或是因为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罗斯遭遇来自贝加尔湖与中国长城之间的蒙古人长期统治,疆土沦作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留下的金帐汗国的一部分,痛失第一时间接触西欧文艺复兴运动之最佳机遇,所以,待到十七世纪末期,亚洲草原势力东遁久矣,俄国已然继承金帐汗国及其周边地区广阔领土,成为横跨欧亚大陆之帝国,彼得大帝遂竭力推行极端西化之改革,努力追回失去的一切。 年轻的彼得,可谓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旅行家。作为帝国沙皇——尽管是“双沙皇”之一,一六九六年之前,他不得不与长兄伊凡共同掌权——却并未对极端保守的东正教传统产生过多“民族自信”,反倒格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