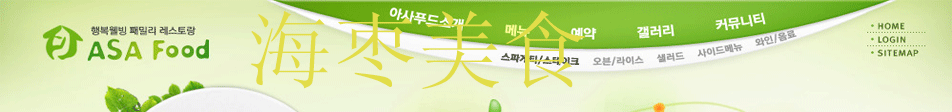|
俄罗斯艺术家VeraShimunia刺绣风光作品 我第一次出国旅游是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冬天,目的地是俄罗斯的海参崴。那是一座毗邻黑龙江的远东城市。隔着N年的岁月远远望去,曾经触目可见的异域风景,大半已经模糊不清了。 但当年遇见那些远东面孔时我的心情,却随着时间的消逝变得日渐清晰。曾经清晰的风景,模糊起来;曾经模糊的心情,清晰起来。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我记得那年冬天,我先是从哈尔滨乘夜行火车,一夜颠簸之后,于翌日清晨到达绥芬河市,然后在绥芬河市转乘汽车,中午左右到达位于中俄边境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附近,在那里过海关。 来接我们的导游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俄罗斯小伙子,个子不高,鼻尖冻得通红,穿着一身显然是在中国集贸市场上购买的假名牌。 小伙子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浑身上下洋溢着这个职业特有的机灵,热情,狡黠,以及旺盛的精力。 他告诉我们,先去吃午餐,午餐后大家可以随意在“戈城”(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简称)转一转,之后再搭旅游巴士去海参崴。 导游的话多少让我感到失望,因为我原以为是坐火车去海参崴。我心里很想看看海参崴火车站。要知道,海参崴不仅是太平洋上的一个不冻港,也是俄罗斯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 西伯利亚大铁路以莫斯科为起点,穿过松树林,跨过乌拉尔山脉,穿越西伯利亚冻土带,横跨八个时区九千二百八十八公里后,最终抵达这里。 我一直对这条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很向往。向往它什么呢?沿途的风景?周遭的城市?不,不全是。 那是什么呢?是向往一种流浪感?一种冒险感?一种在日复一日相似日子的间隙当中,偶然闪现出来的理想主义的什么东西? 也许吧。 毕竟,没有准确答案的人生瞬间,常常有种神秘的美感。 就餐的地方与其说是餐厅,倒不如说是工厂食堂,开阔又冷清,清一色木制的地板和木制的长条桌椅。 在我后来去过的欧洲国家的餐厅里,推开门,扑鼻而来的通常是咖啡,刚出炉的烤面包,微甜的番茄沙司,用黄油炒得略糊的蒜末,和让人有点眩晕的迷迭香的气息。 但这家俄罗斯远东城市的餐厅却是混合着红菜汤,伏特加,羊奶酪,加了香叶的酸黄瓜,以及迫人的冷空气的气息,这种气息在冬天里有着金属般的质感。 做为一个生活在毗邻俄罗斯的哈尔滨的人来说,这是我极为熟悉的“西餐”的气息。这种气息瞬间便让我对“远东”这个地方感到亲切。 午餐后,我们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闲逛。布拉戈维申斯克与其说是“市”,倒不如说是“县”更准确。看着落在小小教堂屋顶上的麻雀,我忽然想起自己的围巾落在餐厅里,就急急地回去取。 餐厅里空空荡荡,只有一个胖胖的俄罗斯大妈正跪在地上,一边大声唱着一首我听不懂,但绝对不在调上的俄语歌,一边用草根刷子“吭哧吭哧”地刷木质的墙围。 她的双手被冷水浸得通红,呢裙一角也完全湿透,但她好像没有感觉,依旧刷得非常用力,刷得一丝不苟,没有半点糊弄应付,也没有半点和谁治气的意思。 刷过墙围,她很费劲地站起来,拎着水桶走到餐厅那一边,继续跪在地上,开始用那个草根刷子“吭哧吭哧”地刷地板。 冬日午后的阳光穿过绿窗框的窗玻璃落在木制地板上,形成一道一道的光影,她就在这些光影中极其认真地刷着地板。 这位俄罗斯大妈在做世人眼中“低微”的工作时所表现出来的耐心,韧性,认真,以及对于整洁的热爱,深深打动了我。 在后来的行程中,我常在公共场所见到那些身材肥胖,但“干活”却一丝不苟的俄罗斯老大妈。 每每看到她们,我虽然并不想上升到“民族性格”之类的东西,但脑海里一定会出现俄罗斯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关于“母亲”的那些深情描写,现在也是。 从戈城去往海参崴的路上,导游一直坐在我身边。我注意到他戴着一条漂亮的银质项链。他打开项链坠给我看,是一张女孩的小照。 女孩看上去很羞涩,黑色卷发,略微上翘的鼻子,鼻翼上是可爱的小雀斑。导游告诉我,这是他的女朋友,名字叫尤利亚,住在新西伯利亚市,他们是在一次校际的交流活动中认识的,两个人打算将来去莫斯科生活。 毕竟,那里是大城市,导游说。 在大城市生活不容易,我说。 他说,没关系,我们年轻,并且相爱。另外这两年当导游,我也攒了点钱。 我说,是坐火车去莫斯科吗?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 他说,是啊,我从海参崴上车,她在新西伯利亚火车站上车,然后我们一起去莫斯科。 我说,真好。 车窗内是导游无比幸福的畅想,而车窗外,则是疾速后退着的乌苏里平原和我飞翔而游离的思绪。 我不知道那些生活在中原地带或是东南沿海的人拥有怎样的地域心情,但对于我这个一直生活在拥有漫长寒冷和寂寥平原的边境省份的人来说,每到冬天,心中便常有苍莽萧瑟之感。 而去另一座与之地域特征相似的异国边境城市,特别是那座所谓的远东城市海参崴,那片原本属于中国的土地,这种感觉便显得尤为强烈。 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瑷珲条约》,令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海参崴便在其中。 所以,在从戈城至海参崴的途中,美丽乌苏里平原的冬日风光,错落有致的山间别墅,飞逝的白桦林大大的眼睛,以及埋藏在这片平原之下巨大的矿藏,便是那样让人感到深深遗憾了。 三个半小时后,大巴车抵达俄罗斯远东最大的海滨城市——海参崴。这里刚刚下了一场雪,车辆疏落,空气清新。这座远东城市与我来说,并无陌生感,因为它有着与我儿时的哈尔滨诸多相似的气质: 相似的建筑,相似的树木,相似的街道,相似的教堂,相似的广场……不相似的是走在这里的,是俄国的男人,俄国的女人和俄国的孩子。 站在码头,太平洋缓然流淌,一群海鸟在庞大而冰冷的军舰周围啾鸣飞翔,远眺俄罗斯太平洋海军舰队所在地――大俄罗斯岛,做为一个中国人,那时的心情,不说也罢。 转角处卖格瓦斯的小亭子的屋顶上积满厚厚的白雪,一对看上去充满活力的青年男女正站在亭子前的雪地里,用大号啤酒杯喝格瓦斯。 姑娘穿着一件腰身纤巧,剪裁非常合体的浅灰色呢大衣,黑色高筒靴,眼睛是如湖水般的深蓝色,睫毛修长而卷曲,头上戴着一顶毛色油润的水獭帽子。 小伙子很高,穿着一条水磨兰牛仔裤,一件红蓝相间的短款羽绒服。同样拥有无比修长的睫毛和深邃的眼睛。 雪后的天空格外清丽明亮,两个人就那样站在明亮的冰天雪地里一边喝着格瓦斯,一边谈着什么,笑着什么,画面像明信片一样美,那是爱情的神态。 熙攘的市场里,一个长相周正,气质颇像前苏联老电影里的布尔什维克的五十多岁的男人,想买中国商人卖的包包。那是一款适合十五六岁小女孩背的包包。 “布尔什维克”递给店家卢布,但卖家坚持卖卢布,这并非是商家的虚报,他们已经僵持很久了。 “布尔什维克”目光非常恳切,我能感觉到他是真心想买这个包包,而卢布也应该是他能力范围之内所能支付的最高价钱。 他的目光让我想起一件久远的,与之类似的,我父亲与我之间的事情。一瞬间,我很想替他付那多出的10卢布,但终究这个想法是不合时宜的。 我不知道那个长相周正,气质颇像前苏联老电影里的布尔什维克男人,最终是否买到了那个包包,但我直到今日也仍然难忘这个人的目光,那是一个并不富裕,但却希望给与女儿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好的东西,同时又拥有端正自尊的父亲的目光。 种族不同,国家不同,贫富不同,但天下父亲的心意,却是相同的。 我们入住的酒店是森林里的一个小别墅群,就是那种林间小木屋。我喜欢小木屋里的壁炉,坐在温暖的壁炉前,一天的冰冷感都消失了,有种想拿着鹅毛笔坐在桌子前写点什么的冲动。 晚上大家一起去酒吧,酒吧里弥漫着矛盾的喧闹和安静。台上有人在唱歌,台下有人在喝酒;台前是迷离,台后是矜持。 一只涂着猩红色唇彩和孔雀蓝指甲油的俄罗斯流莺冷漠地坐在我附近,桌子上放着半瓶波特酒和一只高脚杯。 她一边吐着烟圈,一边等待她的猎物。虽然有那么一两个男人过来搭讪,但显然没有谈拢。 一只棕色的小鹿狗挣脱主人的怀抱在酒吧里跑来跑去,那是一个中国人刚刚在海参崴买的。小鹿狗跑到我们身边,停下来。那个女人看见小鹿狗,忽然站起来,把小狗紧紧抱在怀里。 她喃喃地对小狗说着什么,说着说着,我发现她哭了。我问到导游,那个女人在说什么?导游说,她在说,宝贝,你要去中国了吗?你能听懂中国人说话吗?你想家怎么办呢? 是啊,想家怎么办呢?我也跟着担忧起来。 小鹿狗被主人抱走了,女人又恢复了冷漠。她又坐了一会,走了。半瓶波特酒,一盏高脚杯,一只小鹿狗,涂着猩红色唇彩和孔雀蓝指甲油的俄罗斯流莺,以及,一串眼泪——都在软暧的音乐里消失了。 朋友提议去外面走走,我们叫上导游,打了一台出租车。我们没有目的地,就让出租车司机随意开。 导游告诉我,明天一早我们去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海参崴火车站。司机打开收音机,传来一个俄罗斯男主持人略显沙哑的声音。 导游说,是天气预报,明天会有一股新的寒流从西伯利亚过来,要降温了。 我说,是尤利亚的家乡啊。 导游叹了一口气,担心地说,是啊,那地方很冷的。 我向车窗外张望了一下,心里想,这股寒流很快就会穿越中俄边境的,哈尔滨也要降温了。 一瞬间,年轻的我突然很想思念谁,但我不知道思念谁,就只好盼着明天快点来,好去看看到那条从莫斯科蜿蜒至此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及铁路尽头的海参崴火车站。 谁会从莫斯科乘坐这趟火车到海参崴来呢?我又会遇见怎样的面孔?我无端的期待起来。 不远处居民楼的窗子里闪烁着仿佛碎宝石般的零星光亮。这座远东城市被一种巨大的“覆满白雪的空旷和寂寥”所吞噬。 一时间,没有人说话,原本情绪很高的朋友也突然沉默了。于是,出租车便像一尾鱼,划破沉默之海锋利的寒冷,向更幽深的地方游去。 是的,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平生第一次出国旅游去的是俄罗斯的海参崴,一座毗邻黑龙江的远东城市。 那是很久以前的冬天了。 ——END—— 如果喜欢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