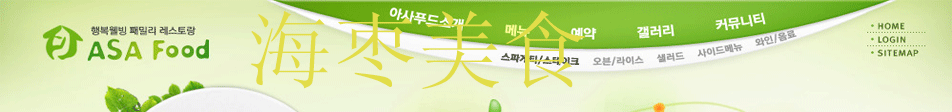|
随时随地阅读就这么简单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绥芬河,这个位于黑龙江东南角、曾被人戏称为“要用放大镜才能在地图上找到”的中俄边陲小城,突然成为举世目光聚集的焦点:3月27日至4月13日,经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入境人,其中人确诊新冠肺炎,还有无症状感染者38人,一时间常住人口仅7万的小城成了抗疫前线。 绥芬河在哪?为什么是绥芬河?这座百年口岸的诞生与发展,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偶然,也孕育着各种各样的必然,从几个历史长河的精选片段中,我们来寻找答案。 ▲4月15日,绥芬河口岸。这也是绥芬河第三代国门。(张涛/摄) 因铁路成为“黄金通道” 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绥芬河铁路交涉局”,绥芬河第一次以一个城市的身份出现在地图上。 如果没有铁路,也许根本不会有这座城市。不过最初,小城与铁路本无缘。 19世纪末,沙皇俄国为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在中国领土上修建了一条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连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 这条铁路原本打算在当时的东宁县三岔口修建,并以东宁境内水系绥芬河作为站名。可修筑中工作人员发现,当地的地质结构并不适合修建铁路,铁路只得向北移动了50多公里,这就是现今没有绥芬河流过的绥芬河市。当时,小城依山而建,林木丰茂,我们至今也很难在文献中准确找到对其之前历史的更多记载。 年中东铁路建成,因其距俄罗斯对应口岸波格拉尼奇内16公里、距俄远东最大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公里的独特地理位置,迅速成为连接东北亚和走向亚太地区的“黄金通道”,这也奠定了绥芬河地区交通、通讯、通商的基础,使它得以与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近乎同步的发展。 据绥芬河市官方史料记载,年3月,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设绥芬河市政分局;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东省特别行政区绥芬河市;年7月,绥芬河公署成立。20世纪30年代,有俄、日、朝、英、法、意、美等18个国家的使节和商贾云集于此,文化和经贸交流异常繁荣活跃,五颜六色的各国旗帜林立市区,时称“旗镇”和“国境商业都市”,并获得了“东亚之窗”的美誉。绥芬河还在中国东北边陲最先开通了火车、汽车,最先有了电灯、电话,被冠之“文明中心”。彼时,来自内地和多个国家的商人有1万多人,常年往来于绥芬河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之间,从事边境贸易,人称“跑崴子”。 在今天已经被改造为中东铁路纪念馆的绥芬河老火车站内,通过一幅幅老照片,我们可以窥探到铁路为这座边陲小镇带来的繁荣,而在绥芬河老城内,一座座俄式建筑,也记录了这座小城曾经的繁荣。 国际红色秘密交通线的建立 20世纪初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催生了绥芬河国际红色秘密交通线的建立,历史赋予了这个边境山城神圣的使命。 年3月,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宣告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为了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上海、北京、哈尔滨设立了交通联络处,开通了从大连海路通往上海,陆路通往北京的交通线。绥芬河地处中东铁路东线,被设立为地下交通中转站。从此,绥芬河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重要枢纽。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此转折点,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研究关于中国命运及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但迫于国内严重的白色恐怖,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最后中共六大确定年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召开。 为了中共六大的顺利召开,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通过哈尔滨、绥芬河、满洲里等地下交通站,接送会议代表过境。据史料记载,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共计人,其中从绥芬河出境的代表有瞿秋白、蔡畅、徐特立、何叔衡、龚饮冰、李文宜、杨之华、方维夏、龚德元等,共计19人。从绥芬河入境的代表有周恩来、邓颖超、李立三、蔡畅、邓中夏、罗章龙、项英、杨之华、向忠发、张国焘、龚饮冰、毛简青等50余人。从此,中共六大与绥芬河这座边境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绥芬河国际红色通道上也留下了光辉足迹。 中国东北开放的一扇窗口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绥芬河人民过上了新的生活。 年,绥芬河军政委员会保卫部接到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发来的《出入国境治安检查暂行条例》及政务院颁发的《进出境列车、车员、旅客、行李、物品检查暂行通则》,经军政委员会研究,绥芬河被认为是中苏边境的一个重要口岸,有设立边防检查站的必要,遂向东北人民政府报告建立绥芬河边防检查站。 年3月3日,经东北人民政府批准,绥芬河边防检查站正式成立。建站初期,这里编制只有11名干部和监护排10名战士。而从绥芬河口岸出入境的人员也较为单一,以苏联军人最多。 年,当时的国务院经贸部授予绥芬河市对苏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权限。山城站在了新的历史起跑线上。从此,田园般的生活中注入了“国际意识”。 改革开放初期,绥芬河还是一个“一条马路、一盏灯,一个喇叭全城听”的万人小城。随着中苏关系缓和,80年代末,绥芬河市开始与相邻的波格拉尼奇内开展贸易合作。贸易一开,绥芬河迅速成为中国东北开放的一扇窗口。 在不断探索中,边境贸易在绥芬河慢慢展开了。年10月26日,绥芬河与滨海边疆区易货贸易正式开通。年1月24日,绥芬河市与苏联对外运输部门首次就开通公路议题进行正式会谈,共同商定开通绥波区间公路。年3月10日,双方举行盛大的典礼仪式,宣告绥芬河市至苏波格拉尼奇内区间国际公路正式通车。至此,绥芬河口岸有了铁路、公路两条通道与苏联对接。 三代国门记录发展脚步 在天长山脚下小绥芬河南中俄边境附近,双方设立一处铸铁手动挡杆,用以规范过境人流和车流,这就是绥芬河的第一代“国门”,现在,这道国门正安静地伫立在绥芬河的中俄边境线上。 已经退休的原绥芬河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恩泰,以前总愿意和老伴一起到绥芬河国门那走一走,看看已经正式投用的第三代国门,再看看已经“退役”的第一代、第二代国门。 “兴边通贸,让绥芬河有了今天。”李恩泰说。 年10月1日,第二代国门落成使用,绥芬河拥有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门。 如果说第一代国门见证了绥芬河现代边境贸易的开始,那么这座集过客、过货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建筑,见证的则是绥芬河口岸的迅速成长。从80年代末汽车临时过货运输口岸到年成为国家客货运输一类口岸,绥芬河在贸易中迅速成长,一个边陲小镇成为远近闻名的“国境商都”。 年8月,绥芬河第三代国门正式开始建设,年底新国门建成。第三代国门高51.8米,长81.8米,跨度54.1米,双向8车道通行,国门主体建筑共分九层,气势雄伟。 站在新国门上,人们可以眺望对岸的俄罗斯和往来中俄两国的车辆、人群,还可以看到手动挡杆的一代国门和已经“退役”的二代国门。 “从铸铁挡杆、到二代国门,再到今天雄伟的新国门,它们记录了绥芬河市的发展,也记录了绥芬河作为中俄经贸往来窗口的日益繁荣。”李恩泰说。 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从来都是绥芬河的使命。 来源 读者报作者 李凤双邹大鹏马晓成郭策赵金龙 温馨 提示 本文摘自《读者报》年04月30日4版。阅读更多精彩内容,欢迎订阅《读者报》。 这就是《读者报》 知过去长知识有谈资摆故事 END 扫码订报 走过千山万水 我依然眷念您 欢迎订阅年《读者报》 邮发代码:61—98 订阅方式 1.拔打或到当地邮政所订阅 2.
|